| 没有了话剧的生活展现出更宽广的舞台和深度参与全情投入的演员 而非情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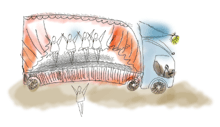 |
| 陆文俊【集团董事办】 |
| 有的地方,去了便会上瘾,比如王府井大街22号的首都剧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对于话剧,我并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个爱好者,甚至近来光说不看,连爱好也愧言。手头两本关乎话剧的书还是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淘到的《老舍剧作选》和《曹禺选集》,其中一本的扉页上有清秀的文字“购于北京?海淀1978.5.2”——之前的保有者应该比我要懂得多。 人艺的剧目总在每晚7点上演,冬天夜黑得早,剧院门口的灯光把立柱打上暖人的橘黄色。此刻的人艺,是绝对意义上的殿堂,人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躬奉其盛。下午草草地吃过晚饭,在中关园搭上804,坐整整两个小时,有几次到了美术馆时已经临近开演,每每有路人甲乙丙丁也在小跑,见到此景,总让人默默一笑。附近的小吃店里也常常坐着来看演出的人,边吃边议论着即将开始的剧目。 那天去看人艺复排的《屠夫》。开演前钟声过后,便可以随着台上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有老演员保证质量的戏让人放心,而且气场合适的话,时常能催化出超乎期待的惊喜。结束时,混身通气,酣畅淋漓。那天是《屠夫》时隔20多年再度登上人艺的舞台。当年的主角都已步入耄耋之年。谢幕的一刻,朱旭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郑榕缓缓走向前,等候他们的是如潮的掌声。年事已高的朱老爷子向看台上的人深深鞠躬,郑榕则不停地和蔼地点头。席间观众为之动容。想起郑老在《西游记》里扮演的太上老君——那个执拂尘的可爱老头——不敢相信时光的锋利。 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去人艺,是香港话剧团排演的《倾城之恋》。全粤语的对白没能阻挡观者的热情,张爱玲的故事和梁家辉的演绎为这部作品吸引了足够的注意。可全剧中最让人动容的倒是歌者低沉的女中音,一遍遍地仿佛吟唱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俗世情歌至今余音绕梁。遗憾的是,全篇的叙事铺陈在梁家辉谢幕时的轻佻一跃打了折扣,很多酝酿已久的情绪在此刻嘎然而止。幸而导演上台感言,言语异常激动。他说自己抱着朝圣的心态登上这个舞台,如履薄冰的担心终于在观众的掌声中化解。导演一口气报出了一串在这个舞台上辉煌过的名字。之后,便已哽咽。 带着舞台的故事走下剧院门口的台阶,和陌生的观众拼车散去。第二天,继续各自的奔忙或闲适。挤在地铁里,外表冰冷,内心汹涌。 换了城市后,住处地处闹市,车水繁华。不远的地方就有剧院,但似乎剧目不多,而且票价也不大亲民。偶尔打开人艺的网页,看着上演剧目的名录,凭空想象,亦自神旺而神往。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因借用《雷雨》的情节与结构而免了很多口水是非,媒介变了,但戏剧张力犹存。 有时候,人明明走出很远,却又好像在原地打转。风日研静的午后,北风清冽的夜晚,有所感但难以言说,要具体而细微地讨论更是要谨慎,这是一种在场的愉悦。虽然看不了演出,但生活的戏剧性总是在一个什么看不见的“地方”,在“那里”——这更是个品之又品的过程。有人说,艺术的目的之一在于“唤醒”。生活广阔而深刻。没有了话剧的生活展现出更宽广的舞台和深度参与全情投入的演员。应该如是,而非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