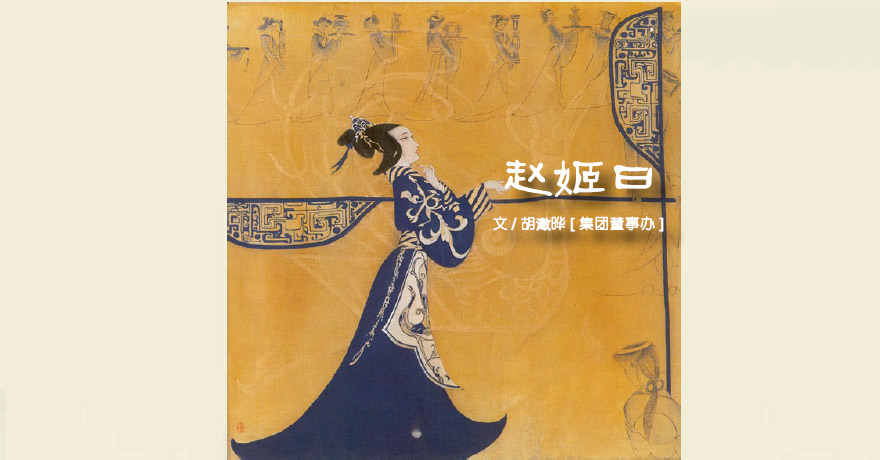不过,“赵姬”这个称谓在当年,在我们战国时期,太让人神往了。“赵女”这个词的万种风情程度绝不亚于今天在欧洲提到“法国女郎”。是的,我是个美女,不然,也没后来那么多的故事。而且,是个能歌善舞的美女。要是在你们今天,我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文工团团员,要是再混得好些可以成为政协委员。可是,在我们战国时期,我的地位很低下,可以被随意买卖;但我从未觉得生不逢时,与很多能歌善舞的美女一样,最终成了皇后。
我不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歌舞家,能有《霓裳羽衣曲》传承后世,况且《霓裳羽衣曲》最终也没能传承后世。我在家乡跳舞,先是被一个珠宝商看上,他买我回家,酒宴取乐之用;后来把我送给了在宴会上看中我的一个人,这个人,从名义上讲,后来是我的丈夫。再后来,我生了一个儿子。关于我儿子生父是谁的猜想,自他出生起,就没有停止过,其著名程度可以与哥德巴赫猜想相媲美。但不管如何,我是他的亲生母亲,是毫无疑问的。买我的珠宝商叫吕不韦,看中我的客人叫嬴异人,我儿子叫嬴政。
儿子在邯郸出生。如果按照出生属地原则,他应该算赵国人。只是我的丈夫异人,一位不得志的秦国王子,后被立为太子,儿子才有机会最终成为秦王。当然,你们今天的人是不管这些的,你们统一叫“中国人”。显然,这得归功于我儿子。但是,在我们战国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就拿后来被我儿子重用的一个大臣李斯来说吧,他是楚国人,虽然很有才干,被拜为“卿”,但由于是外国人,所以只能是“客卿”。他在秦国也缺乏安全感,也会面临类似签证到期等问题,而且他还险些被驱逐出境。
儿子一天天长大,但是教育学在我们那个时代还不发达,况且,王子皇孙之类的教育更加复杂。像慈禧太后找李鸿藻之类的文人教儿子载淳,我很怀疑她是不是把文才和政才弄混了;她也是不得法,总是训斥儿子,弄得母子离心离德,最后白发送黑发,想来也是可怜。明朝的朱翊钧倒是碰到了好老师,张居正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还很懂儿童心理学,编绘《帝鉴图说》,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很是不错。可惜,他如此费心教的学生,在他死后,对他开棺鞭尸、挫骨扬灰,说起来都令人心寒。唉,落后的教育学以及我这个不太会教育的母亲没有对儿子有什么积极的引导,他雄才大略也好,暴戾嗜杀也罢,都是自然而然的。
 儿子13岁的时候就没了父亲,因此,13岁就参加了工作,成了秦王。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每天快乐地玩网游,我儿子却开始终日面对繁杂机要的政务、波谲云诡的外交,以及暗潮涌动的危险。儿子主要只学两门课:政治和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我们那个年代不重视,也没人强调“厚基础、宽口径”,所以都没学。儿子擅长政治,语文一般,所以,还被后人批为“略输文采”。可是,做君王文采不是最重要的,李煜文采好极,最后只能止命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们现在的孩子什么都学,文科、理科、艺术,东方的不够,还要学西方的,一个不够严密的“木桶短板理论”让这一趋势变本加厉;可是,人一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往往靠的是一个人的“长板”安身立命。像我儿子,政治一骑绝尘;爱因斯坦靠物理,尽管小提琴拉得不错,但终究不是帕格尼尼;李太白摧眉折腰事权贵不得,却不影响他“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诗文华章。
儿子13岁的时候就没了父亲,因此,13岁就参加了工作,成了秦王。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每天快乐地玩网游,我儿子却开始终日面对繁杂机要的政务、波谲云诡的外交,以及暗潮涌动的危险。儿子主要只学两门课:政治和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我们那个年代不重视,也没人强调“厚基础、宽口径”,所以都没学。儿子擅长政治,语文一般,所以,还被后人批为“略输文采”。可是,做君王文采不是最重要的,李煜文采好极,最后只能止命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们现在的孩子什么都学,文科、理科、艺术,东方的不够,还要学西方的,一个不够严密的“木桶短板理论”让这一趋势变本加厉;可是,人一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往往靠的是一个人的“长板”安身立命。像我儿子,政治一骑绝尘;爱因斯坦靠物理,尽管小提琴拉得不错,但终究不是帕格尼尼;李太白摧眉折腰事权贵不得,却不影响他“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诗文华章。铜壶滴漏,乌飞兔走,陌草荣枯。儿子走过弱冠少年,成为精壮青年。从29岁到38岁,他用了十年的时间灭了六国。从此,天下以“秦”为国号。盛名远播,从此西方称我们为“China”。儿子统一了文字,因此,在中国不会看到欧洲的街景,指示牌上三种文字,单词主体部分相同,其余部分各有各的花哨。儿子统一了货币,而欧洲自西罗马灭亡之后,要到公元2002年,才欧元一统。欧洲的这些不同,是因为后来他们尽管有过拿破仑、希特勒,却始终没有过我儿子。我儿子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功绩,自然要凸显他前无古人的至尊。他怎么可能像列支敦士登的prince那样,住在简朴的城堡里,每天由王妃亲自开车接送王子公主们上下学。他要修建伟大的宫殿和陵墓,由层层的台阶高高地垒起,巍峨耸立,压迫得令人窒息,万民自觉渺小,不觉已双膝发软,匍匐脚下,五体投地。他还嫌不够,民间焚书,只留医农、占卜。好在多部禁书藏于咸阳皇家图书馆,博士可阅览,并未全烧。否则,当西方谈及他们的修西底德斯(Thucydides)、希罗多德(Herodotus)、荷马(Homer)的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诸子百家了。
关于我儿子的功过是非,历经两千多年的反复讨论、争论、评论,汗牛充栋,史家之述备矣。你们懂的都比我多。
在我丈夫异人,后改名为子楚,去世以后,儿子一直在忙统一、统一、统一,很少有时间陪我,我很孤单,直到遇到嫪毐。他的名字很生僻,历史评价极其之低,儿子嬴政恨死了他。靠儿子赏饭吃的史官以其好恶为是非评判标准,历代沿袭,嫪毐永世不得翻身。但于我而言,那是一段快乐而安详的时光。在吕不韦家里做歌舞女的时候,倘若知道石崇斩美人劝酒的事,你会懂得我的恐惧;与异人在邯郸生活的日子,假使明白身为质子之妻的意思,你能理解我的恐惧;成为秦国王太后之后,如果听过使秦献宝之人图穷现匕刺杀我儿子的消息,你可以体会我的恐惧。我一直恐惧,恐惧自己被杀,自己连同丈夫被杀,自己连同儿子被杀。若有片刻幸福安宁,嫪毐。可是,我是王太后,不能。即使续弦纳妾对于普通男人也算平常事,但丧偶再婚,对于女人,哪怕是我这样一个秦国最尊贵的女人,也是不能。不仅是我,清朝最伟大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仅与多尔衮有点瓜田李下,民间就能“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的满天飞。中国女人境遇如此,外国女人也好不了太多。玛丽•居里,一代科学巨擘,两度诺奖加身,可孀居之恋,足以身败名裂、清誉尽毁。男人即便婚内背叛,女人仍以其姓氏辛勤耕耘,为之扬名四海。权倾天下时留待夫家奥尔布赖特(Albright),低眉顺眼处只是东欧小女人马德琳•科贝尔(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
因此,羡慕唐朝武氏。她不仅不许历史只用个“赵姬”之类的来记录自己,她甚至造出日月当空的字做自己的名字。只是,我写得出来“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样的诗句吗?写不出来。但是,尽管没有如斯才华,却不理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你怎么知道这句话不是赵明诚在看到妻子写下“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后,所抒发的叹服与调侃呢?
儿子嬴政最终杀了嫪毐,车裂,灭三族,惨。我与嫪毐的两个儿子,囊扑而死,惨。从此,母子失和。几年后我郁郁而终,死于咸阳宫。留下了一段关于赵姬的历史记载,以及一个不太好的历史评价。
你们今天,一个孩子唱了一首歌很多人传唱,一个孩子拍了一部戏很多人看过,他们的母亲都以“星妈”之名接受采访。我儿子至少可以排进华夏族最著名人物前五十,我应可以说话;一位在我之前几百年、身前一直不得志的老人,孔丘,每逢开口必用“曰”字,我身前已是王太后,死后追谥帝太后,应可借用之,赵姬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