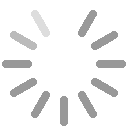文/马淑敏【东阿阿胶】

伟大的文学都是开创性的,它甚至带来某种危险的灾变,在让人惊异的同时又感觉豁然开朗,从文学可能性的角度来谈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种冒险,它会让人觉得自己进入的是已有阐释的巨大丛林,任何言说都有落入窠臼、新意匮乏的危险。但我依然愿意按照读者的阅读角度去诠释这部伟大的作品。

《百年孤独》的核心情节写的是马贡多小镇第一代创始人布恩地亚和妻子乌苏拉在一块空地上建立了伊甸园式的马贡多,以及之后这个家族逐渐兴盛、衰败,最后又在一夜之间消失的百年故事。

《百年孤独》最有独创性和魅力感的点主要有四个:对时间和时间关系的艺术运用,它成为小说庞大构架的重要支撑,而且没有特别的“叙事疲惫”的地方,尽管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死去之后叙事的节奏在变快;在历史、想象、神话和现实之间穿梭,极为精妙地处理了历史、想象、神话和现实之间的“家庭内讧”,让它们重新恢复到兄弟姐妹的关系中;日常的陌生化,惯常事物的陌生化使马尔克斯的小说具备了更为非凡的魅力,在他那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能让我们始终保持着对每一次日出和某双旧鞋子的惊讶感;诗性原则,小说的整体诗性和局部诗性勾联巧妙,有极为充沛的艺术感。
“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就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经典的、反复被作家模仿的一个开头。这一句话不仅仅是展开小说的一个初始的情节,而且容纳了现在、过去、未来三个向度,展示了小说的时空性。
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为自然与非自然、事实和想象、历史与现实重新建立了血缘。在创作中则极为罕见地将心灵感应这一“意向”用客观存在的方式作出具体描述。何塞·阿卡迪奥被人暗杀后,马尔克斯为他流出的血安排了这样的细节:“鲜血从门下边流出来,穿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高低不平的人行道直流过去,流下台阶爬上斜坡,流过土耳其人大街,向右一弯又向左一转,再绕个直角流到布恩迪亚家门前,从关闭着的大门下流进去,为了不弄脏地毯,贴着墙壁穿过客厅,再穿过起居室,在餐厅转个大弯避开餐桌,流经秋海棠长廊,再从正在教奥雷良诺·何塞学算术的阿玛兰塔坐椅下悄悄地钻过去,流进谷仓,再流到了厨房里。当时,乌苏拉正准备打三十六个鸡蛋来做面包”。
另一个令人叫绝的细节则魔幻式的创造,让“充满了责任和鬼火的世界”的俏姑娘雷梅苔丝乘坐床单飞上天空。这是魔法,这是现实中无而想象中有的情节。雷梅苔丝是一种单纯的、洁净的、不谙世事的美,这种美,不属于人间。但小说从来都不是生活生出来的,雷梅苔丝的飞走,其原型是,“她怎么也上不了天。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里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俏姑娘雷梅苔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去了……”同样,在《百年孤独》中曾出现大量的蝴蝶,它在梅梅的头上盘旋,而每当蝴蝶出现,那她的爱人巴比洛尼亚也一定会跟着出现。它也有原型,马尔克斯说,他四五岁和他的外祖母住在一起,有几次家里来了一个换电表的电工,每次他来,外祖母都一面用一块破布驱赶一只黄蝴蝶一面唠叨,“这个人一到咱家,黄蝴蝶就跟着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原型在小说中发展和演变成了什么样子。

日常的陌生化,惯常事物的陌生化使《百年孤独》具备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比如“父亲领着孩子们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箱子里只有一块巨大的透明物体,里面有无数白色的细针,傍晚的霞光照到这些细针,细针上面就现出了五颜六色的星星。何塞·阿·布恩地亚感到茫然无措,只好鼓起勇气嘟嚷了一句:‘这是世上最大的钻石。’……他不知道如何向儿子们解释这种不寻常的感觉,于是又付了十个里亚尔,……而奥雷良诺却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冰块上,可是立即又缩回手来,“它在烧!”
我仿佛是第一次遇到冰,作者使我们“司空见惯”的平常忽然变得新奇起来,而这一新奇和陌生一直都应是文学的,只是被我们忽略久矣。除了见识冰块这一经典细节,还有吉卜赛人带来磁石的细节:“他拖着两块金属锭走家串户,引发的景象使所有人目瞪口呆: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跌落,木板因钉子绝望挣扎、螺丝奋力挣脱而吱嘎作响,甚至连那些丢失多日的物件也在久寻不见的地方出现,一窝蜂似的追随在梅尔基亚德斯的魔铁后面。‘万物皆有灵’,吉卜赛人用沙哑的嗓音宣告,‘只需要唤起它们的灵性’”……假如,这两个细节的例证均是以马贡多人确然的“陌生”为基础的,他们确实是在小说叙述的过程中“第一次见到”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话,我们再看何塞?阿卡蒂奥向弟弟讲述情爱时用的词,“好像地震。”情爱绝不会是舶来品,它不需要吉卜赛人从外面的世界里携带进入,但在《百年孤独》中,它依然具备新颖,陌生和惊讶。

《百年孤独》是一部“创世纪”。有研究者认为,“《百年孤独》以预言和‘世界历史’事件的形式,小说中的第一代何塞·阿卡蒂奥·布恩地亚和乌苏拉离开故乡带着几家人去寻找新的乐园,很像摩西的“出埃及记”。而马贡多的原始建立和发展,则完全是‘创世纪’神话,它从无到有,从荒蛮到初创的过程被描述得趣味横生,生机盈然。原创的马贡多没有警察没有军队,它的一切几乎都与何塞?阿卡蒂奥?布恩地亚的兴趣好恶相联,有某种的田园牧歌的意味,是最初的那座伊甸园。在这里,最初到来的吉卜赛人充当了新知的传播者也充当了诱使夏娃吃下苹果的蛇——和圣经的原初意味不同,外来者带来的可能是潘多拉魔盒,它有种种恶行和惩罚也埋伏着希望和知识的尾巴。而最终马贡多的堕落和毁灭则是末日神话,也是一种启示录——马尔克斯给我们当下写作提供了神话的可能,家族史的可能,史诗的可能。
当然《百年孤独》首先是一个故事,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单单注重故事的生动起伏,波澜丛生,他始终注意着言外之意和故事的深度。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重复融化黄金,制作小金鱼,并周而复始。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且造且毁、且毁且造的这一细节有着丰富的寓意,它暗示《百年孤独》中人物命运和故事策略,暗示生存的循环,暗示存在的某种无意义,暗示上校的孤独,……
小说中,上校的死亡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笔,一生经历几十次战争、几十次失败的奥雷良诺上校在与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对话时曾提到,他打仗更是为了自尊,为了尊严,而他死亡的这段作家狠心剥夺的恰是他的自尊和尊严,甚至坚持不肯让他把裤子提上去。在这里作家显现了他残酷的一面,这一面也是成为作家的必备品质,无论你内心里有多大的疼痛与不甘,你也必须残忍地写下去,将它勾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