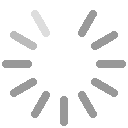扪心自问,有多少年,没有回老家了?
掰着指头数,至少能把每个指头数两个来回。这算背井离乡或是远走他乡吗?谁知道,谁又在百忙之中在意过这个呢?
一个月前,老家的三伯来电“你堂弟结婚,接你喝喜酒”,这是无论如何推脱不掉的。不看三伯的面,看在多年前堂弟帮我打架而在头顶上留下的那个伤疤的份上,我也该回去贺喜。
坐在车上,出了城区,眼睛就显得不够用了。道路两旁,那些不断后退的白杨树,那些不断映入眼帘的稻田、水沟、农用车,都刺激着脑海中残留的关于老家的记忆。
老屋里,那个喂猪的石槽还在不在?村东头,那个堰塘里,是否还有红鲤鱼可钓?虎子家那棵弯成彩虹状的枣树,如今还是红枣飘香吗?灶屋门口的瓦片上,还有晾晒的半干不湿的红薯片吗?
老家,真是太偏僻了。车到终点站后,接着又坐了一程手扶拖拉机才到目的地。
站在村头,望着曾经熟悉如今陌生的村庄,百感交集。还在发愣中,有人在背后喊:“那是小军吧?”回头望去,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立在面前。真的记不起对方是谁了,我只好点头傻笑。对方说:“你5岁多出去的,老家的人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吧?”我说:“是好多年没回来了。”“听小泉说,你今天也回来。你下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要不是你打扮得和我们不一样,我也不敢认你。”“20多年了,变化太大了。”“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打架的事儿吧?哈哈!”“虎子啊,我都不敢认你了。”……
虎子和我,边说边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堂弟小泉家门口。
我赶紧走上前去,向堂弟说庆贺话。三伯,把我迎进院子。问候过后,三伯让我到屋里喝茶,然后继续到外面张罗。
喝了几口茶,我就起身去门外凑热闹。客人们放完一挂鞭炮,就哄闹着给堂弟披红挂彩。眼前的堂弟,身上搭满了红色的被面儿,不停地给客人发烟,新娘子不停地向客人点头微笑。
临近12点时,有人喊:“上礼了!”众人就纷纷进院子,到堂屋门口,奉上“红包”。上礼完毕,院子东头的大锅里也传出香喷喷的菜味儿。很快,就有人宣布:“各位亲朋好友,开席了!十人一桌,赶紧坐好,吃好喝好,吃好喝好啊!”
老家的肥肉,块儿真大,老家的锅巴,味儿真好,还有那散发着淡淡香味的米汤。饭桌上,我和虎子坐在一起,我们相互敬酒。饭后,头有点儿疼,本打算找个地方躺一下,虎子非扯着去他家坐坐。
同龄的虎子,已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爹了。媳妇是邻村的,比他小三岁,看着也算是个贤惠的人。说话间隙,四处张望,没有发现那棵彩虹状的枣树,也没发现他家灶屋的瓦片上晾晒的红薯片。
聊了一个多小时,虎子丈母娘喊他去干点农活,我就起身告辞。走出他家,想都没想,就径直往村东头走。
堰塘,是徒有虚名了。满眼都是干裂的土块,土块之间的缝隙可以伸进去大拇指头。小心地溜下去,望着一人多深却空无滴水的堰塘,嗓子眼里干得慌。
爬出堰塘,走过记忆中那口全村人赖以生存的水井,发现井口盖了块厚厚的大石头,想必里面也没有什么内容了吧?最后,回到曾经生活的老屋跟前,情绪立刻就凝固了。
屋子的黄土墙,已经脱落得不忍心去碰触。两扇门板,已经摇摇晃晃。屋顶的青灰瓦片,已经开始发白。灶屋西侧的猪圈,已经消失,只有那个依旧存在的长方形石槽证明着猪圈曾经的存在。所幸的是,屋前那棵枣树,尽管无人照料,依然倔强地生长着。
望着望着,视线就模糊了。
当夜,堂弟家请了戏班子,庆祝大婚。亲戚朋友们,纷纷解囊点戏,表示祝贺。
躺在床上,乐器声、唱戏声,让人无法入睡。但满世界的热闹都已与我无关,我用被子蒙住头,脑海里却不断闪现出30多年前那个穿着开裆裤、挂着两筒清鼻涕,满村子乱跑的小孩儿。伸出脑袋,翻个身、紧闭一下眼睛,泪水终于洪水一样暴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