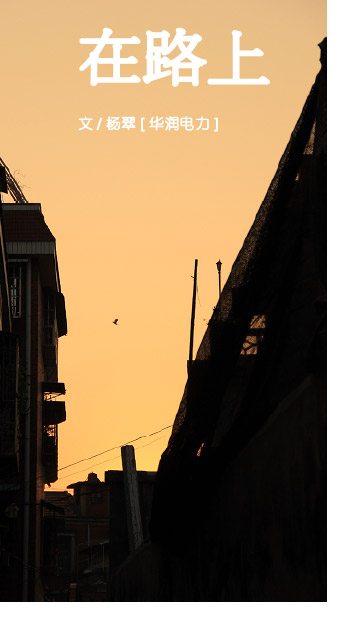
开完会,走下乐凯大厦,冬夜的寒冷迎面而来,我拉紧风衣,走过百思买,经过第一八佰伴,看到华润时代广场,看见坐落在广场街边的星巴克。只为了再看看,浦江绚烂的灯火,朋友的别来无恙,我来到滨江路,我走过东绣路,来到浦建路,我走进上海广场,经过徐家汇,在陆家嘴徜徉。只是一个过客。十年来,我行走在陌生的路上,与无数陌生人遇见,把这一切当作自由。
几个老朋友,还有一个深圳的前同事,我们在2006年几乎同时爽快地从那家外企辞职,他来上海后再没见过。去年的时候,朋友们大多单身,现在雨已经领证,见面那天刚陪老婆试完婚纱;S和Z已经有了女朋友,男人们全都有了归宿;佳和我一样,将二十几年的单身坚持到底;L刚在上一个周五,孤单地祭奠离婚一周年;云的追求者依然在排着大队等待。女人们还在寻找归宿。现实耐人寻味,“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某人的日志里,摘录着一句不知出处的话。
朋友们像从前一样健谈,时间没有留下太多痕迹,无论是面上,还是表达出来的思想。或者我们都长大了,用一种貌似平静的方式,不曾改变的眼神,问问过往,有多久聊多久,却在离别的时候,不带一丝的遗憾。高兴的是我们别来无恙,坦然的是我们来日方长。欢声笑语中,彼此还剩下多少情感,只有自己知道。
离开了深圳,除了同事和家人,电话很少响起,深圳的朋友知道我不在,以节省漫游费为名,不再来电问候。金山区的亭林镇,早上的阳光是清冽的,我吃着街边的南瓜炸糕,喝着热豆浆;行走在下午5点漆黑的路上;拉开旅馆窗帘,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夜空,繁星点点,大地上没有什么灯火;我在来之不易的寂静与黑暗中睡去。
 嘉兴的旅馆中,跟妈妈通电话。妈妈正在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电视,得知家里的温度1-12度,和嘉兴一样,我心中莫名地温暖起来。十年都在南边,很少与家人同时感受同样寒冷的气候,突然间似乎离家人近了一些。告诉妈妈我买的蓝花布鞋,有着线纳的底儿,妈妈说她会,年轻时也做过,突然想张口要一双红布鞋。不知什么时候我终于大了,不好意思再跟妈妈撒娇,却通过狡猾的方式,寄情思于物品中,将爱随身携带。我不会织毛线,不会做鞋,缝补衣服也很笨拙。偶尔闪过一些念头,想和妈妈一起,晒晒太阳,漫无目的地聊天,做饭,闲暇时候让她教我这些,但终究一闪而过。有些事情其实不遥远的,没有心去做,便离你很远了。
嘉兴的旅馆中,跟妈妈通电话。妈妈正在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电视,得知家里的温度1-12度,和嘉兴一样,我心中莫名地温暖起来。十年都在南边,很少与家人同时感受同样寒冷的气候,突然间似乎离家人近了一些。告诉妈妈我买的蓝花布鞋,有着线纳的底儿,妈妈说她会,年轻时也做过,突然想张口要一双红布鞋。不知什么时候我终于大了,不好意思再跟妈妈撒娇,却通过狡猾的方式,寄情思于物品中,将爱随身携带。我不会织毛线,不会做鞋,缝补衣服也很笨拙。偶尔闪过一些念头,想和妈妈一起,晒晒太阳,漫无目的地聊天,做饭,闲暇时候让她教我这些,但终究一闪而过。有些事情其实不遥远的,没有心去做,便离你很远了。几天后,嘉兴某个纺织厂的车间里,厂工正在出售羊绒制成的围巾,我透过斜射进来的阳光仔细检查瑕疵,然后填写速递单。家人和朋友,以“生日快乐”之名,或者没有任何名义。也许,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有意义,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名义。
不断地看着倒退的风景,我走进各式各样的旅馆,推开某一扇门,将行李翻开,把物品摆满整个房间。早晨出门前,习惯性地告诉前台和楼层服务员,除了垃圾,其他的东西不能动。不换床单,不铺床,不整理沙发和桌上杂乱的物品,包括洗手台上的瓶瓶罐罐,甚至一块随意摆放的毛巾。我要再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切原封不动,没有改变。因无论怎么杂乱,当再次回来时,总被整理得一成不变的房间,提醒我,一个在路上的陌生人,身处陌生的别处,陌生得好像不存在。
想起某个朋友说过:我知道,自己尚且肤浅,对于四法印,我还只感悟到“一切情绪皆苦”,但我却已相信,“我是一个漂泊的人”。在这浮动迷离的流年,走在不知名的十字路口,等待行人灯变绿,晴朗的冬日阳光灿烂,眯起眼睛仰望蓝天,似乎又听到胡德夫伴着海潮的歌声。最早的一件往事,最早的一个故乡,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件衣裳。




